|
|
 发表于 2020-1-23 20:35:35
|
显示全部楼层
发表于 2020-1-23 20:35:35
|
显示全部楼层
来自: 中国北京
一觉起来,武汉确实封城了,其实在下一月4号发帖时认为这种极端情况也只是口头阐述的最坏结果,不幸,但我们不妨通过封城的手端读出背后的目的,如下
仅为个人愚见
①春运还在继续,gf只能通过强制手段改道,所谓“保胆取石”暂且只能封城,规避往后散播风险。
②从确诊数来说,hen you ke neng jiang ji xu ying lai pen yong shi zeng zhang er qie zhe ge shu zi bu shi yi dian ban dian,ti qian zuo hao guan men keng sha de cuo shi zhun bei,bing qie dang quan guo ge di lu xu fa xian bing li hou,qie duan yu bing yuan di de lian xi,zhen dui bu tong yan zhong cheng du diao qian ren li wu li,zhu ge kong zhi xiao lv geng gao
③还有一点,我觉得是为了不引起恐慌,武汉的消息更新,如果是封城后,实时情况可能没那么。。。。transparent,军心为大,我理解
以上为1.23
————————————————————
各位,现在的情况是①+②,赶紧出城,保护好自己,捂严实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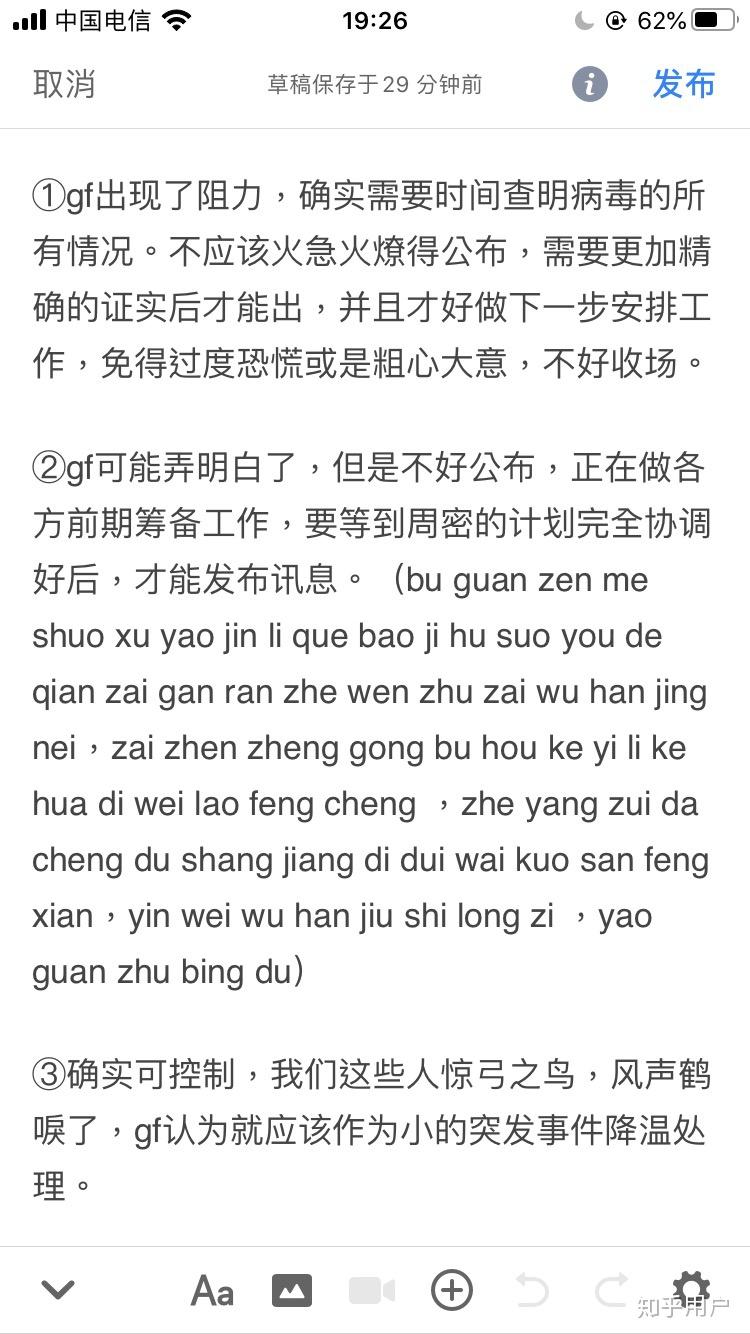 ———————————————————— ————————————————————
资本,是具有嗜血性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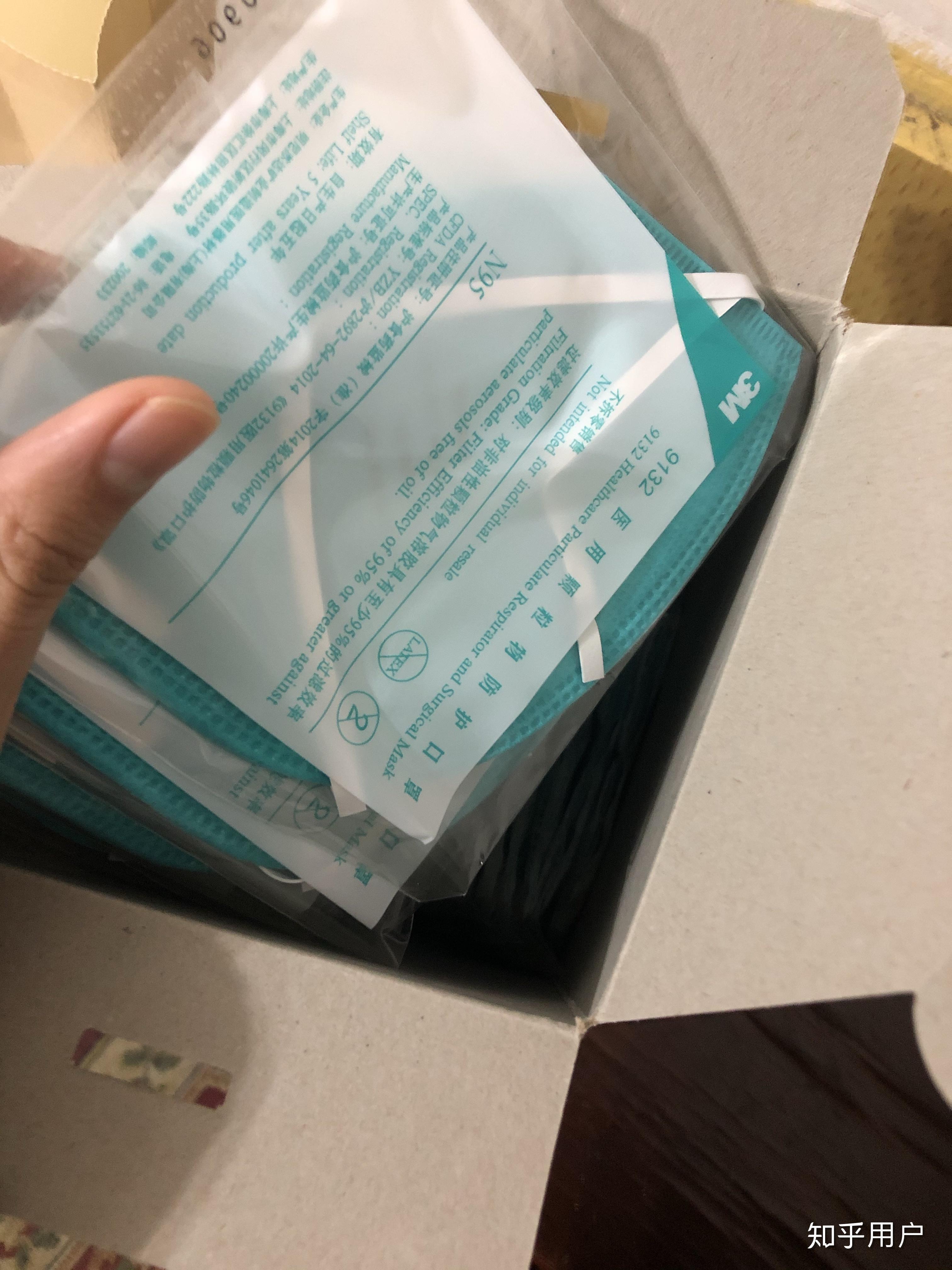 ———————————————————— ————————————————————
真不知道某乎是个啥意思,非要逼我删一些正常言论? |
|